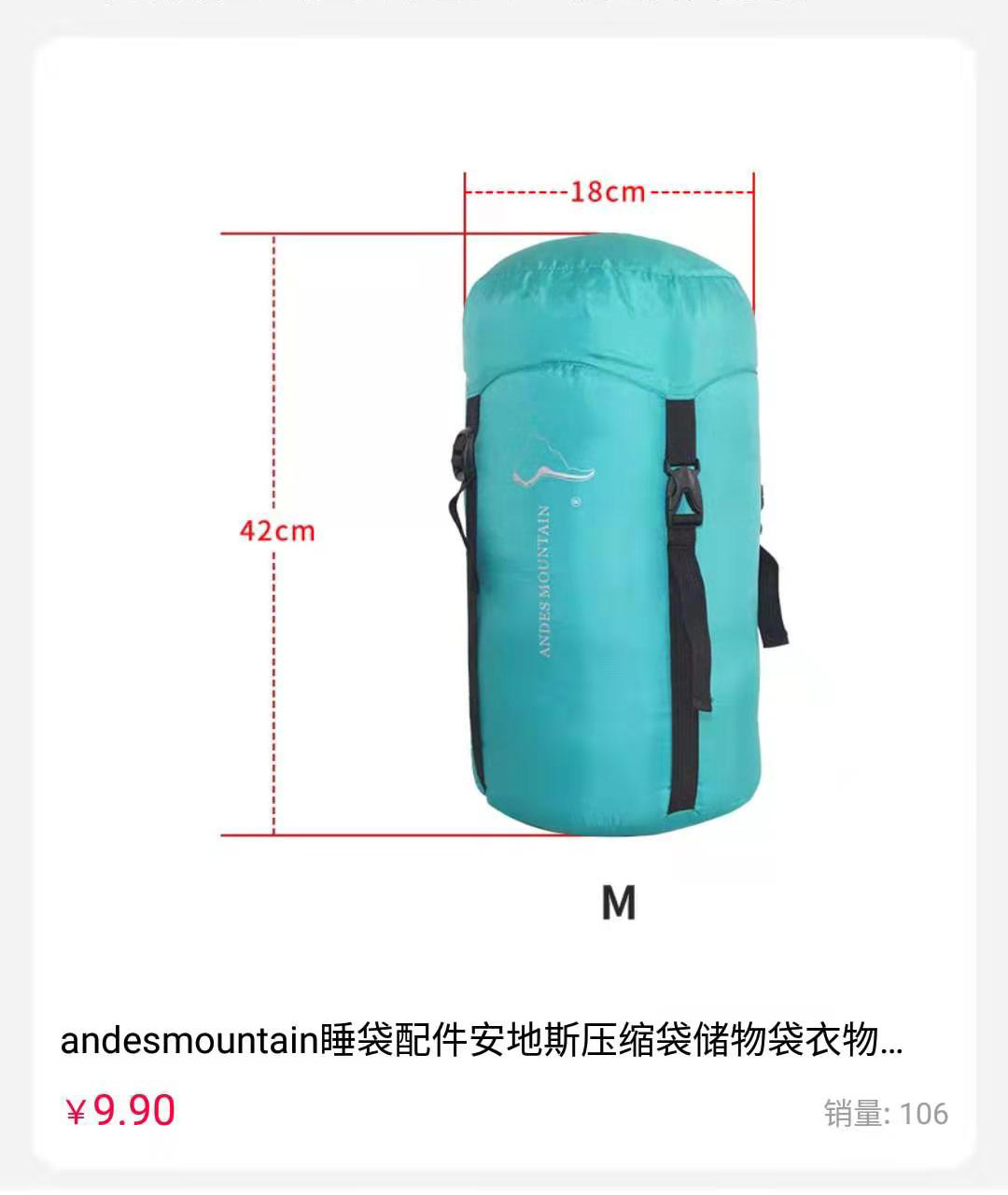凌晨的黑暗像是魚網般將大地牢牢的捕獲,想從縫隙逃脫卻發現密集的雪花襲來。即使雙耳都掩蓋上厚暖的毛帽與巖盔保護著,但寒風依然不甘心的呼嘯來去,把雪片像是子彈般擊打在包裹全身的科技布料上,叮叮咚咚的像是激光四射的流彈。而頭燈的光束像是揮舞的光劍,引領著我一步一步的進攻。
蹣跚的步伐搭配著激烈的喘息,直到宛如某種宣告般我堅定的把頭燈按熄把冰斧直插入雪地,頓時各種形狀的雪花一片一片的佈滿四周不再如涌浪般灑落。寒風失去了消息,天空宛如果凍般微微搖晃蕩漾著不透光的漆黑。所有一切的一切就在瞬間停止了下來,我坐下喝著熱咖啡,溫燙的液體持續熱暖我的身軀,直到她就這樣悄然地出現。
你要回去了嗎?在那片黑暗中,她伸出雙手摩挲著我的臉頰,讓我凍的直打哆嗦但內心其實激動莫名。即使你以微笑冰封大地,我還是充滿信心可以看穿那對酷寒的雙眸;即使你以寒冰遮蓋面容,我還是充滿熱情勇于嘗試輕咬你沒有溫度的嘴唇。就算我知道你的心永遠不會為了我而解凍,但我仍將奮力向前,試圖博取你的青睞,就算只有一眼、就算只有一吻。
我好想好想大聲說出口,說無論如何,我都心甘情愿的為了你接受任何追求你可能會面對的各種下場,甚至像其他永遠沉睡在你懷里的許多人一樣我都無怨無悔。難道你不明白我對你的心意嗎?
但我微笑著,反正女人心我永遠都搞不懂,不如以退為進,打定主意就是不讓你猜透我內心燃燒的欲望和執念。我把保溫壺蓋旋緊、把頭燈扭亮、把冰鎬再次握入手中……
2006,夏季7月。

大地依然包含在黑暗的帷幕里,列車一陣晃動并在一聲沉重的嘆息之后停了下來。離開臥舖走到開啟后的列車門邊,因為是暫時停靠所以不讓旅客下車。
凌晨4時許,我在新疆烏魯木齊往喀什路上的中途小站~阿克蘇。望著列車外稀零的幾點燈火飄搖在迷濛薄稀的夜霧中,帶上耳機聽著崔健的花房姑娘,1989年的花房姑娘,到如今還能稱呼姑娘嗎?如果此刻走過我身旁,不知道她是否仍舊是我14歲時引頸仰望的美麗模樣?
凌晨的低溫從列車外擁襲而來,我旋開保溫壺把熱咖啡吞入喉,當那份溫暖流淌進入身體之后,以為帶來了抵抗寒冷的堅強,但沒想到,也帶出來了那份身處遙遠異地的違和特異之感,讓孤獨飄零的滋味在一瞬間全部涌現。
把山區的地圖攤開,看著窗外的夜幕宛如拉開夾鏈般讓光幕逐漸呈現,不知道接下來的路途,將被寫出怎樣的故事情節呢?我無從預測,所以我忍不住激烈的想像著,用雙手危危顫顫把冰鎬從背包拿出來,那尖端抖動著的,是期待和興奮的震盪傳遞。
沿著蜿蜒的中巴公路上抵帕米爾高原的攀登前哨站~蘇巴什村,此處海拔3650迷,一下車高山反應就如燈下的影子般悄悄纏繞了上來,始終再也沒能擺脫。略作休息后徒步前往海拔4550米的大本營(BC),之后就是某種規則與節奏的攀登與適應行程。而隨著日程的推進與疲累度的增加,高山反應的頭痛逐漸擴大。加上身處多國混合隊伍,自己在其他人和同行的兩位學弟的眼前下意識地筑起了形象的高墻,甚至可以感受到空氣中那股~雖然不是相互”較勁”但確實的”比較”心態。
私底下和深交多年的學弟說話雖然肆無忌憚,但依然免不了要表現學長的自信和強悍。這人際關系網就像拔河一樣把我弄的心力交瘁,而我一向習慣主導自己的攀登節奏,勉強配合這個以軍事準則為風格的主辦協會則讓我如被捆縛般心有余而力不足。全部加起來就像風暴一樣把我扯得支離破碎。掌握著周遭外在與自我內心的種種線索和跡象,我開始感覺這一次要達成圓滿結果的可能性逐漸降低,要說失望當然免不了,但偏偏我這人從來就不是能一次就把事情做好的人,好比過往的戀愛一樣。
總之,雖然每一天每一天都讓我意志逐漸消沉,但身處這高山,心靈很難不被深深吸引與震撼,終究,我就是為了這個而來。
BC設在充滿碎石與冰河的交接地形,在這里一如世界上其他的熱門高山,聚集著各國的帳篷,待在BC的悠閑日子可以看見形形色色的事情發生,親見從高地營跳飛行傘下降至大本營的膽大心細,和表演藝術團一起搖擺共舞的輕松忘我,或是待在廚房和廚子依薩姆丁他抽煙我吃西紅柿比手畫腳的閑談。
宣布正式沖頂行程開始,首日目標是第一營(高C1),海拔5850米。山徑沿著碎石坡上行,一般隊伍會在雪線前設定C1,但我隊則在此處的裝備帳篷換裝,繼續翻越陡坡后到達我們設置的C1。

這里位處一平臺,約略可容納3個籃球場大小。晚上的帳篷之夜,在我的強烈要求下和向導扎西交換了隨身聽,頓時不用再聽他哼唱著支離破碎的張振宇的不要再來傷害我這首歌,原先以為的因為高山反應加劇所以頭痛欲裂的狀況也馬上減輕許多。
隔日行程為推進到第二營(C2),同樣我隊的C2設的地點硬是比一般登山隊的高一些,海拔約6650米。

路線已由先行的隊伍標志出來,沿著紛亂雜踏的足跡行進著,幾處冰裂縫的確保點確實,故不難通過,所以C1之后我就換上冰爪,走起來爽快俐落多了。

在C2休息一日之后,繼續推進至位于海拔6950米的第三營(C3)。隨著海拔上升,頭痛更形嚴重,攀登隊伍分成三個梯次,抵達C3發現第一梯隊因為天氣不好全都擠在營地等待,所以原先的帳篷馬上爆滿。度過了混亂而擁擠不堪的一晚之后,凌晨向導宣布沖頂開始,幾乎沒睡的我著裝跟著幾位欲沖頂的隊友一起出發。
勉強走了幾百米吧,終于還是決定撤退了。想到做出這樣惡劣天氣卻要沖頂的決定、想到大本營的糧食與運補計劃簡直糟糕又愚蠢……嘆了口氣搖搖頭我把冰鎬插入雪地、把頭燈按熄,藏族向導扎西問我怎么了?我隨便找了個借口決定撤退,畢竟我沒辦法說出口~『因為我感覺不對嘛!』互道珍重后彼此轉身朝各自的方向走去。
飄雪無止無盡的落下,或是消融或是堆積,我重新開啟頭燈,并把冰鎬拔起準備下行。打算先回到離我最近的C3,然后以最快速度一路下撤回BC。我不再能如前幾年到阿拉斯加爬Mt. Danali(又名麥肯尼峰)一樣待在高地營追蹤天氣然后抓住機會攀登沖頂。那時我正年輕,也正享受著一個人獨登的樂趣。作出撤退的決定對我來說沒什么困難的,和結婚這件事比起來簡直是一片蛋糕的程度呀!
每一位登山的人內心深處都有一座神圣的山峰,也許是最孤高的、最遙遠的、最艱難的。但對我來說,最神圣的,永遠是~那些暫時還沒走上頂峰的。
但即使到了頂峰,又會有什么呢?
其實,什么都沒有,依然只是純淨的白雪、湛藍的天空與窘迫的喘氣。而且會有很大的機率,當下無法親臨最高的那一小塊地方。可能會被突然變化的氣候勸退、可能會被終于崩解的體能擊潰、可能會被無從預測的落石雪崩打敗、可能會被細菌病毒馴服。
即使一切都接近完美,在拋擲了青春、燃燒著夢想、遞送出金錢、備齊裝備與體力技巧之后,喘著氣一步一步走到山頂,在那里等著我的,不是酬償、也沒有彌補;不是黃金珠寶、也沒有顯赫名聲。
所擁有的,只有微小命運和富饒大地交會時的贊嘆,以及看似孤注一擲其實豐盈盛滿的生命體驗。但即便把自己內心所有世界的感動說出來,那化為語言的諦觀,對旁人來說終究只會是一片虛無。

離去前,山之女神溫柔的輕聲問我:你會回來嗎?
回到中巴公路旁肥沃豐盛的草原的蘇巴什村,冰爪沾黏的白雪已然融消、登山杖刺出的只有空氣中的休休空響。我把一些攀登裝備送給駐守當地的旅行社女登山者,然后借了她的自行車一個人在草原上漫無目的騎著,一邊聽著Maroon 5(魔力紅)的『she will be loved』這首歌的時候,開始坐在草原的一塊角落里情不自禁地放肆地哭泣著,雖然我到現在還是無法明白究竟是內心的不甘?還是不舍?
等終于收拾好情緒時就繼續漫無目的騎著,我的家已經離我太遙遠讓我忘記了方向。經過一個毛氈蒙古包的時候,在門口的她掰了幾片剛烤好的馕餅給我,我則把帶去的糖果零嘴全給了她。我和她的家人閑聊著,并一起拍了一些照片,

離去前,阿依加瑪力嬌羞的輕聲問我:『你會回來嗎?』
帕米爾高原的雪雖然看不見但已深深地埋藏著我的懷念,下山后不耐煩當地協會的觥籌交錯,便和義氣相投的攀登隊長艾山風塵仆仆的搭了出租車到其家鄉游玩。參觀了棉花田、扒著農家飯,吃著看似樸素但是風味超絕雋永的羊肉串、喝著菊花茶。

離去前,艾山的姐夫維吾爾老大哥斯文的輕聲問我:你會回來嗎?
新的旅行家像是一個來去孤單的影子,對旅行地沒有重量,也不留下影響。大部分的內容發生在內在,不發生在外部。
第一位到達北極的美國探險家-羅勃?培里(Robert E. Peary,1856-1920)曾向北極圈的原住民-愛斯基摩人請求幫助,他們反問他:『為什么要去哪里?那里什么都沒有。』
地理意義上的闖入、突破與征服的西方探險特質,是二十世紀初期強國的信仰價值觀,但對于愛斯基摩人而言,才不管你什么極地極心,對他們而言,有用的才有意義,有海豹可以獵捕的地方,才是有意義有價值的地方。
而關于登山,我們從來不需要對別人解釋什么,正如同我們并不需要一一對旁人說明我們的所做所為,甚至向別人證明。
反正,我們的”海豹”都在不一樣的地方等著我們去捕獲。
不過才不管誰懂不懂,我自己依然會繼續追尋下去,去尋找下一個傲然切割天空一角的山頂天堂。因為我曾經見過,站在頂峰天堂那一端的山之女神,那顧盼之間的絕塵一笑。
這么多年過去了,直到現在,聽見穿著冰爪踩在雪地上的嚓嚓聲,仍然會讓我如同面見心儀的女神般小鹿亂撞般的怦然心動。
生活中充滿著各式各樣的目標,但對我來說,目標真正的意義是~只要還有做夢的能力,就能讓我們在生活中努力地去創造理想的藍圖。真正去實踐才會發現,那不一定會讓我們的生命更富有,但我可以肯定的是,那賦予了我生命的意義。不論那夢是什么。
也許是再次登頂、也許是陪著孩子們平安健康的長大;或許是更高更遠的山、或許是握著太太的手在小漁村里漫步生活。
我踩出的每一個步伐,都將引領我走向屬于我的天堂,免不了經過懸崖、走過裂縫,總是要付出很多很多,我才能來到靈魂渴望的那一條山徑上,總是有些夢會在遙遠的地方、難免有些夢恰好在云端。
這里只有~潔凈的白雪、湛藍的天空、冷冽的空氣……

如英國詩人丁尼生的詩句:去奮斗,去追尋,去發現,永不屈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