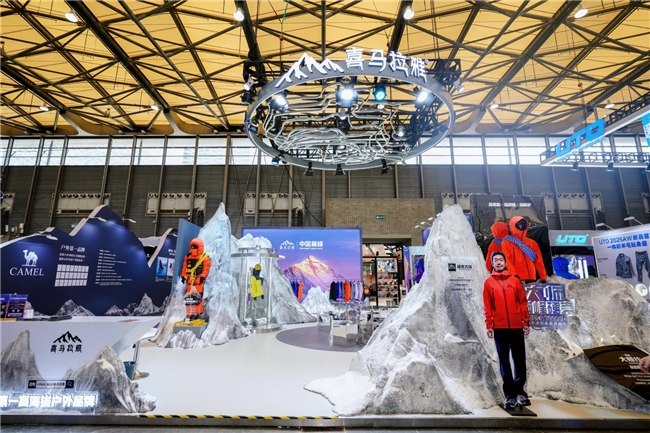我們總在等待明天和日出,總在尋求希望和未來,總在寄寓高山和大海,上天、入地、登山、潛海都成為各類文學影視作品表現的內容。法國文學家讓·里卡爾杜的“古典小說是對冒險的敘事,現代小說是對敘事的冒險”,前半句說明了這個事情,尋寶、復仇、科幻、西部、警匪都是冒險,穿越火線、火星救援,碧海藍天、柴米油鹽,甚至愛情都是一場冒險,而且最后往往感慨,“人生何嘗不是一次歷險呢”。
“人類為什么要攀登高峰?”
“因為它就在那里。”
這是英國登山家喬治·雷·馬洛瑞給出的標準答案,1924年他登上珠穆朗瑪峰的北峰后再也沒有下山。
有三部電影登上了珠峰,分別是李石勛導演的故事片《喜馬拉雅》、巴塔薩·科馬庫導演的故事片《絕命海拔》和蕭寒、梁君健導演的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
《喜馬拉雅》改編自2005年的真實事件;《絕命海拔》根據美國作家喬恩·克拉考爾所著的《進入空氣稀薄地帶》改編,故事源自于1996年的真實事件;《喜馬拉雅天梯》則將鏡頭對準西藏年輕的登山向導,歷時四年,完整記錄了珠峰北坡登頂全過程。
三部電影皆立足于“真實”,所以可以先從事實的角度梳理一下三部作品。

《絕命海拔》

《喜馬拉雅》

《喜馬拉雅天梯》
1853年,珠峰被勘測為世界最高峰,海拔為8840米。100年后的1953年5月,英國登山隊有兩名隊員沿東南山脊路線登上了珠穆朗瑪峰,向導是尼泊爾的夏爾巴人。1950年以前,大多登峰者都是從西藏境內沿北坡攀登的,西藏解放后因其重要的邊防位置而禁止外國登山隊任意進行登山活動,所以他們改道尼泊爾。直到1956年,瑞士登山隊第二次登峰后,標注了珠峰高度8848米。
1988年,韓國登山運動員嚴弘吉登頂珠峰,其后12年,登完了卓奧友峰、希夏邦馬峰、喬戈里峰、馬卡魯峰、洛子峰等所有世界8000米以上的14座高峰,成為世界上第八位、也是亞洲第一位完成這一偉大壯舉的登山家。韓國電影《喜馬拉雅》的主角正是這位登山家,由黃政民飾演。他在韓國有著“民族英雄”一樣的地位,電影中也透露出大韓民國的國家民族主義,當他們再次冒險登峰救人時,呼叫美國、歐洲、中國的團隊,沒人應答。
從1953年到1993年,40年中只有400多人次登峰;從1993年有商業登山以來,已經6000余人次登峰。《絕命海拔》中的主角新西蘭著名向導羅布·霍爾就是業余珠峰登山指導商業概念的提出者,1996山難的兩個團隊一個是霍爾的“探險咨詢”,另一個是美國的斯科特·費希爾組織的“瘋狂山峰”公司的登山隊。
1994年,尼瑪次仁萌生了創辦登山學校的想法,經過五年年各種準備才基本完成。
1999年,西藏登山學校正式成立,從此打破了尼泊爾的夏爾巴人壟斷高山協作的局面。
紀錄片《喜馬拉雅天梯》鏡頭對準的就是這所學校,歷時四年,記錄了這群為登山者搭天梯的向導——大山的孩子。

攀登高峰常常被另一個詞語替代——“征服”。
人類中心主義的思維方式就是這樣,直到平權運動和生態美學興起,我們才開始思考人的位置。
現在,當你看到一個人遛狗,稱呼它為“兒子”時,不再想到“馴服”,而是人與動物和諧相處。
三部電影在“人與山”的關系上表現出不同的態度,《絕命海拔》中羅布·霍爾認為“珠峰是一頭難以馴服的猛獸”,這時候自然的一個“待馴服”的野獸,人作為主人的地位顯露無疑。當雪崩、暴風雪和缺氧的災難來臨,這頭猛獸吞噬了兩個團隊的十幾個人。
《喜馬拉雅》中的嚴弘吉則非常排斥“征服”這個詞,這個從小在山腳下長大的登山家來說,登峰不過是“運氣好點,得到山的允許,短暫停留在山頂而已”。說這句話時的登山愛好者嚴弘吉是謙卑的,人與山像是需要磨合、交流的朋友,山脾氣好的時候,人在山上小憩了一下。
《喜馬拉雅天梯》中的向導們登峰前則需要到海報5100米的絨布寺接受洗禮,那樣能得到“守護神的保佑”。珠穆朗瑪峰,藏語意為“圣母”,藏族先民的原始自然崇拜中,山神是基礎。他們世世代代在青藏高原上繁衍,崇山絕嶺都有神祗和精靈存在。即使在后來,當佛教傳入藏地,全藏區政教合一的時期,山神在藏區的民間,仍是人們主要信仰的神靈。

現在看來,“人類為什么要攀登珠峰”呢?
是征服的欲望,是虔誠的信仰,甚至也是奢侈的時尚。
然而電影中卻展示了各種對現實生活的逃避,《喜馬拉雅》里的樸武宅(鄭宇飾)要爬好多山,卻沒辦法面對女友;嚴弘吉成了大英雄卻做不好丈夫和父親;《絕命海拔》中有個在現實中潦草生活的道格拉斯,寧肯死在珠峰之上。
而他們不也像《海上鋼琴師》里不肯下船的1900,《碧海藍天》中長眠大海的恩佐嗎?而他們不也像難斷家務事的清官、忠孝不能兩全的將軍嗎?廳堂、廚房、高山、戰場,總有一個是你的珠峰。
文藝青年都有窮游拉薩的情懷,為何鮮有攀登珠峰的夢想呢?
這三部電影沒有告訴我們,西藏圣山登山探險服務有限公司公布的消息或許能解答這個疑惑:2016年春季珠穆朗瑪峰登山活動總費用RMB330,000元/人。33萬元人民幣的費用包含:登山期間的住宿,伙食,交通,高山氧氣、保健隊醫、向導、協作、高山攝影、后勤保障、牦牛、環保、修路、登山注冊、景區收費、營地設施等費用,并未包含一切個人性質的消費及個人技術裝備和服裝費用等。
“問世間是否此山最高,或者另有高處比天高”“在世間自有山比此山更高,但愛心找不到比你好”,不斷攀登、不停冒險,最后回歸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