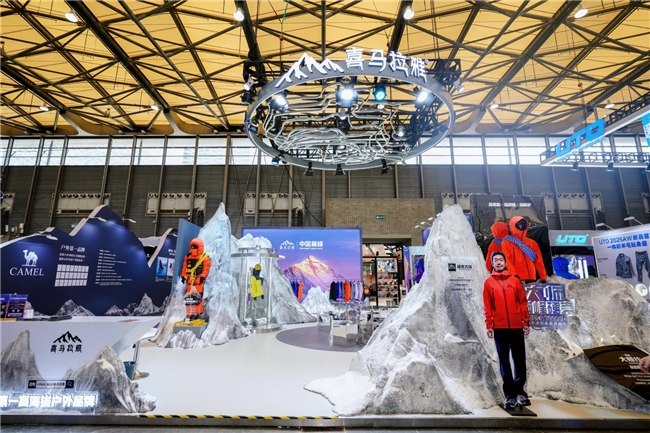有人說,在這個世上如果你想絢爛的死去,那么就去登頂珠峰。
登頂珠峰即使在目前來說,也是一份巨大的榮譽和挑戰,對于一個登山愛好者來說,能夠成功登頂珠峰一次,你就擁有了“獨孤求敗”的資格。
如果有人花錢贊助你登珠峰,你會一試嗎?
攀登珠峰的死亡率約為7%,即每100個攀登者當中就有7個死亡,對比交通意外平均每10萬個人就有約17個人的死亡率為高。
關于珠峰的電影也有很多,像《Into Thin Air》進入空氣稀薄地帶、《Everest》絕命海拔、《Beyond The Edge》飛越邊緣,也看了很多有關珠峰的資料。第一部與第二部電影講述的都是同一個災難,就是1996年兩個登山隊伍因為人為以及天災的原因,導致包括兩名開始把登頂商業化的知名珠峰向導(Rob Hall羅布·霍爾和Scott Fischer斯科特·費舍爾)及其他登頂者死亡的事件。為什么重拍?主要因為《Into Thin Air》是由知名作者Jon Krakauer喬恩·克拉考爾以親身經歷的觀點敘述整件意外,但事后遭很多人指其報道不夠全面、主觀以及不準確。《Everest》除了根據Jon Krakauer喬恩·克拉考爾的故事,也加上生還的另外兩個人寫的自傳來敘述整件事。
這次意外,是天災也是人禍,即使是登了頂五次的Rob Hall羅布·霍爾也因為心軟,受一位已用了太多時間登頂的團友拖慢,最終在接近登頂處遇上暴風雪而葬身珠峰。另外印象深刻的是在8,000米以上的珠峰地帶竟然出現了大堵車,主要因為同一時間要登頂的人數眾多,而山路狹窄,這亦是很多人太遲到達頂峰的原因之一。

《Everest》劇照。
而《Beyond The Edge》則是一套劇情式紀錄片,講述了1953年Edmund 埃德蒙·希拉里和Tenzin Norgay丹增·諾爾蓋成為全世界上第一人登上珠峰的經歷。最深刻是埃德蒙·希拉里說他不是征服了珠峰,而是珠峰讓幸運的他能站在它的頂峰上一會兒而已。謙虛的他實在讓我感到十分敬佩!因為不同于現在每個登項者均有夏爾巴人為其背負裝備,甚至有夏爾巴人為其在最難的Khumbu Icefall上搭鐵橋,甚或用直升機送上Camp I,在埃德蒙·希拉里的那個年代,他和Tenzin丹增可真是用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地從大本營爬上頂峰。
留在珠峰上的尸體,基本上在272個葬身珠峰的人中,逾200具尸體仍在山上,有一些依然未能辨認出身份,有一些則成了人們登頂的地標,也有些則成了一們登頂的阻礙。

《Beyond The Edge》劇照。
人們要登上珠峰的目的是什么?1953年埃德蒙·希拉里和Tenzin均屬于英國的一枝珠峰探險隊,領隊的是一位陸軍上校,乃當時第九支試圖成為第一隊能登頂的隊伍。當他們成功登頂后,剛巧是伊麗莎白二世加冕的時刻,整個登頂充滿政治與帝國主義意味。
在《Everest》中,前郵差Doug道格·漢森已是第三次登頂,他希望借助自己的故事,告訴身邊朋友即使一個平凡人如他也能攀上珠峰,那世界沒有什么是不可能。日本女登山家Yasuko南波康子則已攀了世界六個洲的最高峰,珠峰自然而然成為她要攀上世上七大洲最高峰的最后一個目標。
每個人都有其要登上珠峰的原因,就像有人的夢想是組織家庭、生兒育女;有人的夢想是環游世界、周游列國;也有人的夢想是事業有成、買樓買車等。夢想是主觀的,其他人很難評論是否值得。例如每個攀珠峰的人均要付出約7萬美元(約50-60萬元)的費,你說這些錢可以用來環游世界幾個圈,我說這些錢可以用來為建兩、三間學校,他卻寧愿用這些錢來登珠峰,每個人的價值觀均不同,怎么比較呢?
不過,我倒想大家思考一下當自己在珠峰上遇到需要被幫助者時,是否真的要見死不救?經典的例子是2006年英國登山者David Sharp,他成功登頂后,因為極度疲倦,從頂峰下降約450米后便坐下來,不久更被凍結了(還未斷氣)。超過40個正在登頂的登山者,雖然經過他面前,在無論是以為他死了,抑或不想阻礙自己繼續登頂的原因下,都對他見死不救。
當然,在登山者體力透支,自己沒能力下山的情況下,絕對是他自己的錯誤判斷,與人無尤,不能怪責見死不救的人。但若在自己有能力,卻為了自己成功登上珠峰的夢想,而不去盡力搶救身邊垂死的人,這則倒值得我們反思在我們要實現夢想的同時,是否可兼顧對弱者施以援手?
網上有太多有關討論,我倒想說說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Everest》電影里,雖然前郵差Doug在登頂后已倒下,但Rob Hall怎么也要把他拉下山,即使眼見暴風雪來臨,他也拒絕見死不救。另一隊的向導,Scott Fischer斯科特·費舍爾已完全虛脫,同行的夏爾巴人Lopsang拒絕丟下他不顧,最后是Scott要求Lopsang下山去找助手Anatoli Boukreev求救。而Anatoli,雖然救不了Scott,卻獨自在黑暗的暴風雪中拯救了另外三名團友。

約4600米的Dughla,看到多個為紀念葬身珠峰者而成立的佛塔,當中包括1996意外的Scott Fischer斯科特·費舍爾。
既然連珠峰登頂都商業化了,吸引每年約400人去攀爬它。徒步珠峰大本營的路線每年已吸引約2萬2千人,以每年只有6個月適合徒步而言,即每天均有1千多人走在這山頭里。在山上,我不時聽到徒步者投訴人太多,嚴重破壞大自然。但另一方面,我也聽到夏爾巴人感恩珠峰大本營的生意養活他們一家人。

往珠峰大本營路上不時出現大堵車。
夏爾巴人主要聚居在約3600米的Khunde村莊,在埃德蒙·希拉里于1953年登珠峰前,讓夏爾巴小孩接受教育的學校一間都沒有。其后,埃德蒙·希拉里為夏爾巴人建立了很多學校、醫院、機場,慢慢這個地區也發展成徒步旅游區,這條路上直至5,000米以上的所有旅館、茶館和挑夫,基本上都屬于夏爾巴人。
但又有誰愿意像夏爾巴人一樣抵受嚴寒和惡劣的氣候,在5,000米以上開旅館?又有誰愿意用頭頂托著那30公斤的物資,一步一步把徒步者需要的食物運上5,000米(而他們一日只能賺取約7美元)?又有誰愿意把意圖登頂者一步一步帶上珠峰頂,又帶回大本營(而他們搏命的整個登頂過程的人工也只不過是1萬美元)?

夏爾巴人聚居的Khunde村。
所以沒有誰對誰錯,要發生的就要發生,珠峰已無可避免地充滿徒步者以及登頂者,而他們亦養活了很多自力更生的夏爾巴人。重點是如何最得平衡,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徒步者以及登頂者,減少對當地人文及生態的破壞,例如尊重當地文化、宗教以及環境,也要努力盡環保的責任。珠峰路上布滿被棄置的氧氣瓶以及破爛的裝備和帳篷已為人詬病,更被世人取名為世上最高的垃圾場。
其實在每個成功登頂的人背后,也有一個或更多個的無名英雄夏爾巴人,也有如埃德蒙·希拉里所說的珠峰的恩賜珠峰讓幸運的人站在它頂峰一瞬間。